【书香民革读书月·心得展播】千年风骨——读《世说新语》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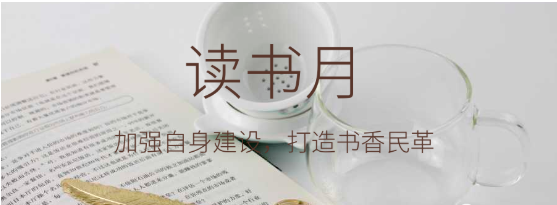

民革鼎城总支、鼎城一中高二政治老师 刘小平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魏晋,有个裙裾翩飞的男人,顺着屈子的足迹在兰皋椒丘边悠游,赤足,怀揣一本破破烂烂的、卷了毛边的书,他有时仰头凝望天边停遏的白云,有时兴之所至在书上涂涂画画,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了泥里也并不在意。树荫下偶尔有闲谈的农父朝他投来神经质的眼光,此刻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不修边幅的男人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南郡公刘义庆,也还不知道----就连刘公本人也无法预料---他怀里的书将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个比宋武帝要响亮得多的名字,它叫《世说》,后称《世说新语》。
你见过钟鸣鼎食之家里多情葬花的女儿家是不是?你游过嶙峋的赤壁和波云诡谲的朝堂,阴谋阳谋的谋士将臣三分天下是不是?当然,《世说新语》格局与气象全不是那样,它没有三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杀伐决断,没有盛唐富丽宏大的万千妩媚,它只是夹在两个恢宏时代之间一幢不起眼的房子,住着一群放诞不羁的士人,在魏晋的离乱动荡下唱着一曲悠悠扬扬的小调,一直飘到好多年后的今天。
什么是魏晋风骨?可以说,《世说新语》就是魏晋风骨。
山阴的雪很大的那个晚上,王子猷抱了一壶暖酒,满眼都是白色,兴之所至,他突然就想到了好朋友戴安道,二话不说地撒开脚丫子乘船就走,他一边乘船悠游一边与雪对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思及此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船行一夜,最终连戴安道的门也没敲开。又比如那个独乘鹿车,携一壶酒,说“死便掘地以埋”的刘伶,那个喜欢在竹林里打铁,死前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绝响的嵇康,那个因为念及家乡的菰菜和鲈鱼说辞官就辞官的张翰……这些行为放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可笑之举,然而它独独发生在《世说新语》里,独独被刘义庆所记载,好像便格外能体现出一群士人的洒脱随性,一个时代的不羁与自由,让人神之往之。
《世说新语》里住的的从来都是鲜活的凡夫俗子。碧瓦朱甍过眼云烟,几人记得征战一方的君王姓其名何?几人能忆起长河边的烽火狼烟?然而王公名士的嘉言懿行,奇闻逸事,却借由这不大不小的房子一齐漂流到了今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侯在十六世纪就能霸气地喊出“beyourself”的宣言;“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嵇康之约堪称当代社恐人尬聊之最;“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和妻子一波狗粮从古代喂到了现代,可以见得,《世说新语》里鲜活的思想和情感使人悟然,不论古今,人的喜忧都是相通的。
由此便足以见得作者的伟大与高妙,刘义庆也许无意写魏晋风骨,却在三言两语中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他也许无意和众谄媚,却仍做到了在百年后的今天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大了说,他是历史的展卷人,时间的普罗米修斯,往小的方面看,他是一栋房子的建成者,或许呕心沥血,或许无心插柳,总之,他为魏晋超脱的衣冠士人铸就了一个有趣的,活色生香的灵魂寓所,而且还不收房费。
逆着血液洄游,目之所及皆为风流,顺着掌心的纹理攀登,不用伸手就碰到了过往,如果《世说新语》已经融于我们的血液,我们肌肤的每一寸纹理,那么它是不是也同样热烈地,奔放地绽放在民族的心野上?冯友兰先生将它当做“中国人的风流宝鉴”,可以窥见,它确在中华民族重礼遵教的民族性格之外,独立地竖起了别具一格的高楼,成就了民族骨性中为数不多的宝贵的狂放恣意。
在一千六百年的奔流中,一本书是如此脆弱,一盏不起眼的烛灯,一阵足以吹散线装的大风就能轻而易举地毁灭它。然而士人的风骨与哀乐,民族的秉性与节操却又如此坚固,在刘公踩过的泥土地上,生发不息地绵延出千千万万个一千六百年。

